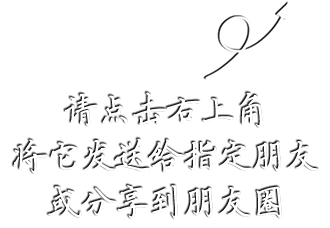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当晚,珍妮·埃彭贝克以《帕尔马修道院》的主人公法布里斯·德尔·东戈的方式度过了这一夜。法布里斯·德尔·东戈发现自己身处滑铁卢战役的混乱之中,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周围正在发生着这样的事情。那天晚上,Erpenbeck和一些朋友见面,并在他们的一个家里睡了一觉,那里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话。直到第二天早上她才从收音机里听到所发生的事情。人性的决定性时刻就在几个街区外发生,而她却错过了。
35年后,埃尔彭贝克可能是德国最受评论界和最受欢迎的作家,她在国际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甚至可能比她在国内的名气还要大),有一天她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那个人性的决定性时刻——欧洲最后一丝真正乐观的曙光,自由战胜独裁的胜利——改变了她的生活,也改变了数百万东德人的生活。也许,这就是她那一代的作家和这个国家当前文坛的其他人物,他们继续思考那个夜晚和随后的变化,希望和失望。在某种程度上,这一事件的阴影笼罩着埃本贝克的所有作品,但在她的最后一本书《凯洛斯》(Kairos)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凯洛斯于2024年获得了著名的布克国际奖。
“一开始,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很自由,我们可以购物和旅行,”Erpenbeck在一个寒冷的秋天早晨说。她和丈夫住在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的公寓里,她的丈夫是一名奥地利指挥家。普伦茨劳贝格是旧东柏林最具智慧和波希米亚风格的社区。但除了解放之外,至少在她的记忆中,柏林墙的倒塌还有别的意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结束和它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吸收是一种损失:失去一个国家,一个不复存在的国家。“没有讨论社会主义或不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经历了我们国家的崩溃,或者一个国家的崩溃。”

这个故事——一个曾经消失的、如今几乎是想象的国家,一个曾经属于他们的新国家的喜悦和失落——解释了今天德国的许多问题和一些神经症。这是一个关于东西方持续分裂、著名的“精神墙”、持续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以及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民粹主义力量的故事。有时小说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能更好地解释这个故事,比如英戈·舒尔茨和乌维·特尔坎普等作家的作品,以及埃尔本贝克本人和《投影仪》的杰出作者克莱门斯·迈耶(Clemens Meyer)等现象。《明镜周刊》(Der Spiegel)将《投影仪》列入上世纪100部最佳小说名单,并认为这本书是经典之作,尽管这本书刚刚出版。
这种力量来自哪里,这种风格,这些主题让一些评论家认为这些书是德国作家最吸引人的作品?为什么东方文学会成为关于1989年是什么以及它在今天意味着什么的最激烈辩论的战场?
这是耶拿周五的夜晚,这里是诗人和思想家的故乡,歌德和席勒的故乡,和滑铁卢一样,这里也是拿破仑的战场。今天,它和欧洲其他许多城市一样,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城市中心,有商业街,偶尔会有一家烤肉店,晚上7点后没什么事可做——也许除了花8美元左右的钱去图书馆听一位作家演讲。
“这本书是一件大事,”这位资深文学教授向约90名观众介绍迈耶和“投影仪”们时说。“这是本世纪的小说。”
几天前,迈耶挑起了一桩丑闻,使单调的德国文坛活跃起来。这件事发生在德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奖——德国文学奖(Deutscher Buchpreis)的法兰克福颁奖典礼上。《放映者》是一部一千页的小说,迈耶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才完成,它涵盖了20世纪和21世纪德国和欧洲的一大片历史。这部小说入围了决赛,但评审团最终选择了《嘿,摩根,你得到了什么?》(嘿,早上好,你好吗?)玛蒂娜·海夫特。
离开典礼时,迈耶惊呼道:“该死的混蛋!”就连小报《图片报》(Bild)也报道了这句话。在《明镜周刊》(Der Spiegel)上,作者澄清了他如此愤怒的原因。该奖项往往会促进图书销售,他认为这笔钱将有助于支付他的离婚费用,并偿还他欠税务机关的近3.68万美元。他又向评委会扔了一枚飞镖,说:“如今,伟大的文学作品不再受到重视。像我这样的书,涵盖了整个世界,是阿尔弗雷德Döblin和格内特·格拉斯传统的虚构镜头……”

迈耶并不缺乏谦虚。2006年,他以描写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莱比锡的小说《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al wir träumten)一举成名。“我知道这首童谣,”它令人难忘的开场白写道。“有时我默念,有时我只是开始哼唱,甚至没有注意到,因为记忆在我的脑海里跳舞,不,不只是任何记忆,柏林墙倒塌后的那些时间,我们联系的那些年?”
他也不需要野心,不需要与伟人比肩的意志。《塔》(The Tower)是另一部巨著,故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共产党晚期德累斯顿(Dresden)的资产阶级背景下。特尔坎普在给El PAÍS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没有提到迈耶最近的“不赞扬”。“《投影仪》可以与格内特·格拉斯的《锡鼓》和韦·约翰逊的《周年纪念》相媲美,或者,对读者来说,可以与哈维尔Marías或罗伯特Bolaño的《明日之脸》相媲美。”
在耶拿的读书会上,以及当天的谈话中——下午在咖啡馆里,晚上在啤酒馆喝酒时——迈耶谈到Bolaño和斗牛;克里斯塔·沃尔夫、布丽吉特·雷曼和沃尔夫冈·希尔比格等对他产生影响的民主德国作家;以及他对柏林墙倒塌的记忆。当时他12岁,住在莱比锡,他的父母曾带他参加过一些抗议活动,尤其是在莱比锡市内,这些抗议活动加速了纳粹政权的终结。迈耶已经有了文学抱负。“那是一段疯狂的时光,”他说。
“20世纪90年代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看到身后,看到民主德国曾经的样子,也可以看到我们面前的样子。我利用这种自由阅读了所有1989年之前我无法阅读的文学作品。《铁皮鼓》不是在东方出版的,”他说。“我的一部分永远是东德作家,但只是一部分。”
来自西方的作家不可能写出《当我们在做梦》,因为它与迈耶青春期在莱比锡的经历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同样,很难想象来自斯图加特、汉堡或德 塞尔多夫的人会想出《放映者》(The projtors)这个故事,它讲述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的故事,引用了由德国作家卡尔·梅(Karl May)的畅销小说改编的西方电影,这些小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取得了巨大成功。
Meyer说:“2008年我在克罗地亚旅行时产生了这个想法。作家兼战地记者埃多·波波维奇(Edo Popovic)带我去了上世纪60年代拍摄卡尔·梅(Karl May)的那些奇怪的西德电影的地方。我立刻认出了这些地方,因为小时候,我是这些电影的忠实粉丝。作者向我解释说,30年后,在他们拍摄电影的同一地点,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爆发了第一次冲突。那时我就想:‘这是一种强大的材料。我必须做点什么。一个人可以用它来写一部关于战争和历史疯狂的伟大小说。1941年,德国人摧毁了南斯拉夫。1962年,他们又回到了电影行业。30年后,南斯拉夫沦陷,爆发了内战。”
如果说迈耶身上有什么东德特色的话,那可能是他的视野,在时间和空间上既边缘、宏伟又全景式:“我处理的是20世纪伟大的乌托邦。蒂托这样做了,但在那里也不起作用。1989年,在莱比锡,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与历史非常接近的人。历史发生在那里,这是非常独特的。”
在莱比锡尼古拉教堂(Nikolaikirche)前的一家咖啡馆里,巴赫曾担任该教堂的音乐总监。今天早上,管风琴手正在演奏普罗科菲耶夫的《彼得与狼》(Peter and the Wolf),这是1989年和平革命的核心,德国音乐家德克·奥什曼(Dirk Oschmann)回忆起那些日子。他也被历史感动了。奥希曼当时是一个沉浸在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中的学生。他的注意力分散在音乐家阿德里安·勒弗尔khn的流浪和电视新闻之间。“一本德国书,”他总结道,“一本讲述德国哲学、德国苦难、从路德到希特勒的漫长德国历史,以及浪漫主义、新教和艺术的作用的书。”所有这些问题都间接地出现在1989年。当然,我问自己,‘我现在知道了什么?’”为了近距离体验历史,他和女友坐火车去了柏林。他把德国联邦政府发放给东德人的100马克花在了Suhrkamp平装书上,其中许多书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买不到的。“我很清楚,一切都将彻底改变,”他说,“对我来说也是如此。”
Oschmann现在是莱比锡的现代德国文学教授,出版了《东方:西德的发明》。这是一篇关于东德身份的文章,以及在柏林墙倒塌近四十年后,它如何仍然被负面含义所笼罩,并被定义为“偏离”常态,即“西德”身份。

一方面,东方文学拥有奥希曼所说的“独特的叙事资本”——独裁统治下的生活、1989年的革命、20世纪90年代的艰难转型——这些都是西方作家所缺乏的原材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生活如此缺乏革命、悲剧和英雄行为。另一方面,散文家谴责这种文学是如何被锁在西方建立的旨在贬低它的贫民区里的。他谈到了1989年前在西德获得崇高认可的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等作家,是如何突然被贴上“感伤和道德庸俗”的标签的,这是一种迎合共产主义政权的文学。其中一些作家与邪恶的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Stasi)之间的联系被曝光,给他们的声誉埋下了最后一颗钉子。
“民主德国文学的概念被破坏了,就像来自过去的东西一样,”Oschmann说。“而且它还在继续损害来自东方作家的文学作品。”
回到柏林,在埃尔彭贝克堆满书籍的办公室里,谈话继续进行。埃尔彭贝克自己也写过一本小说,讲述了民主德国的终结和统一后德国不确定时期的开始。她的书《凯洛斯》通过同情政权的知识分子汉斯和学生卡塔琳娜之间关系的破裂,记录了一个国家的解体。“一切都在分崩离析,”Erpenbeck写道。她讲述了在纳粹统治时期,许多德国作家,从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到托马斯·曼,是如何离开家园的。后来,相反的情况发生了:他们的家园抛弃了他们,他们根本没有去任何地方。
当Oschmann哀叹民主德国文学的概念如何继续被用来对付当代作家时,他指的是历史学家Ilko-Sascha Kowalczuc对Erpenbeck的批评。在《自由的冲击》一书中,和埃尔彭贝克一样在东柏林长大的科瓦尔丘克回忆起了这位《凯洛斯》作者的家族根源,并似乎在为此责备她。Erpenbeck的祖父母Fritz Erpenbeck和Hedda Zinner都是二战期间流亡到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战后,他们成为东德的知识精英。Kowalczuc认为,这使他们的孙女对他们消失的国家的看法更加温和。“对她来说,1989年不是庆祝自由的日子,”科瓦尔丘克写道。
“当你评论的时候,你应该看看我的其他书,”Erpenbeck回应道。在我们的谈话中,她从书架上拿出一本《自我反省》(Selbstbegragung),这本书是她的祖母海达·津纳(Hedda Zinner)于1989年出版的,对她在斯大林主义的俄罗斯的岁月进行了批判。她说,她的祖父母的生活比科瓦尔丘克描绘的“共产主义狂热分子”的形象要复杂得多。无论如何,她说,“人们必须承认,我和他们隔了两代人。”
《凯洛斯》触动了人们的神经,是现代德国身份认同中的一个亲密的地方,因为它关系到1989年的意义。解放,是的,还有民主、繁荣和福利,在这个星球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但也有挫折和创伤。
Erpenbeck从书架上取下了更多的书。关于苏联时代的书,弗里茨和海达的30年代。20世纪90年代的几卷照片,其中醉酒与未知的眩晕交织在一起。像Sibylle Bergemann这样的照片说明了这篇文章,目前正在柏林C/O画廊展出。它展示了1990年的波茨坦广场,一个人拿着一个可能会飞上天空也可能不会飞上天空的风筝,东西之间的无人区,标志性的广播塔。一个瞬间,一个时代。
在她的散文集《Kein Roman(非小说)》中的一篇文章中,Erpenbeck写道,尽管她今天享受着所有的舒适,但一丝悲伤仍然存在,这是经济利益无法消除的。她问道,你能想象吗,即使在一个永远被称为流氓政权的国家,一个人怎么可能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她喜欢认为这是可能的,一个现在已经消失的国家存在是可能的,在今天几乎是想象的,在那里曾经有可能感到满足,即使一切最终都失败了。她喜欢相信,除了“激进的消费主义、激进的个人主义、激进的利己主义”之外,还有另一种模式。这是什么?她在位于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的公寓里说:“我当然不会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消失而哀悼,我认为任何人都不会。”“可是——我怎么能这样说呢?”我认为,人们之所以感到悲伤,是因为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
 微信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