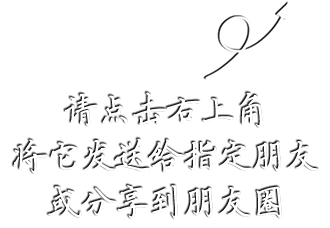Edo Costantini开玩笑说,帮助他与艺术家Delfina Braun结婚的人是金熊奖得主。那是2007年,他们都在柏林电影节上,展示他制作的电影,她也参与了这部电影的合作。“我们去柏林是因为我们有一部电影在竞赛中获得了最高奖,所以我们不结婚是不可能的,”他说,听起来像是童话故事。德尔菲娜深情地纠正他,用她的目光把他带回现实。“嗯,我们马上就相爱了。但我们在巴西的贫民窟拍摄,这是一次非常紧张的经历。那是我们第一次一起旅行,”她解释道。
这部电影被穆Padilha精英队伍,这是一个伟大的巴西国际成功的电影,也是一个伟大的个人成就江户,曾寻求解放自己从他父亲的影子,爱德华多Costantini,拥有最大的财富之一在阿根廷和最好的当代艺术收藏之一在拉丁美洲,以及拉丁美洲艺术博物馆的创始人布宜诺斯艾利斯(MALBA),其中江户主任多年。
17年后,江户和德尔菲娜在艺术上和个人生活上都保持着卓有成效的婚姻。他们刚刚在曼哈顿的Praxis画廊成功闭幕了一场名为“鸦片耳语”的展览,该展览由布劳恩主持,但康斯坦蒂尼和建筑师德尔菲娜·穆尼斯·巴雷托(Delfina Muniz Barreto)也合作过。这种经历让他们在特权和精英统治之间的冲突关系中得到了重申。
“我从小就很努力,没有人给过我免费的东西。当然,我非常感激并为我的父亲感到骄傲,他给阿根廷留下了一座博物馆。因为有太多的商人积累财富却不回报任何东西,”科斯坦蒂尼说。在他的艺术生涯中,包括电影平台和制作公司Mubi,艺术和出版倡议Kolapse以及实验音乐专辑Silencio等项目,他遵循为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的指导原则。他总结道:“醒醒,治愈创伤。”

这一原则也是它们存在的原则。他们和四个儿子幸福地生活在纽约北部的贝德福德。在接受EL PAÍS采访的秋日,他们在色彩斑斓的落叶林中买了一套不太豪华的房子。在这个地方,他们以自己的形象和肖像创造了一个世界,一个自然的阳台,这是他们最终的缪斯,他们试图在每次散步时破译,每次有动物来到他们远离疯狂人群的避难所。
“作为一种文明,我们已经与大自然分离得如此之远,而大自然却不断地以它的威严和力量召唤着我们,”两人中更善于交际的布劳恩解释说。科斯坦蒂尼更孤僻、更孤独,更珍惜自己的空间,他补充说,在这所房子里,他们已经意识到“在每一个出生、每一个死亡中都能看到的那种神秘”。然后他补充说:“我拍过植物和蘑菇,还有许多德尔菲也画过的东西,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然后每一幅画都以不同的方式代表它。”对她来说,推荐信来自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或塞西莉·布朗(Cecily Brown)。对他来说,从Gego或Lygia Clark那里。
在这个他们分享的研讨会上,他们的差异和共同点以一种越来越和谐的方式聚集在一起。一方面,德尔菲娜(Delfina)拥有丰富的创意,她在2022年举办了第一次专题展览后,又回到了普拉希斯(Praxis),她的鸦片花炭笔画散发着一丝不苟,看起来几乎就像一本植物图集中的作品。“小时候,我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区,大自然是我的自然栖息地。我是父母的独生子女,所以我有很多时间是一个人度过的,我喜欢收集植物。我有我的日记……这就是我对分类和了解每件东西是什么以及它的用途的痴迷的来源,”她回忆道。当她学习心理学时,她专注于心理健康,并在成瘾研究方面实习,同时阅读荣格和他对集体无意识的研究方法。“身心康复一直是我最大的兴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紊乱,它从何而来。从那时起,我开始对鸦片产生兴趣,这种植物具有治疗、麻醉的作用,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这种迷恋是她与丈夫的联系之一,因为10年前,他们都在曼哈顿下东区的一家书店里发现了让·谷克多(Jean Cocteau)的《鸦片:戒毒杂志》(Opium: Journal of Drug Rehabilitation)。科斯坦蒂尼更专注于视听——最重要的是音乐、电影和摄影——通过他改编的电影《美女与野兽》(1946)了解了这位多才多艺的法国艺术家,并立即着迷于他的作品,当他在钢琴上弹奏他的一首乐谱时,他的右边就有前面提到的那本书。这种协同作用是纽约展览的起源,Delfina最强大的领域(绘画)是由一个中央青铜雕塑补充的,就像罂粟在开花过程的不同时刻的森林,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植物的声音被放大了,人类无法察觉。
Costantini解释说:“有了一个装置,你可以听到植物、蘑菇发出的频率……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迷人的项目,因为绘画传达了一件事,雕塑传达了另一件事,声音赋予了一切事物另一个维度。”这个展览将成为2025年让·科克多在南美洲的第一个单一主题展览的一部分,展览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Niterói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

尽管他的谈话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充满重要人物的过去的残余——从他设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MALBA举办第一届尚塔尔·阿克曼回顾展,或者当他第一次听到伊夫·科切特的“崩溃学”科学,这启发了他的一个项目,与派蒂·史密斯一起组织慈善音乐会——江户承认,他的沉思生活试图完全专注于现在,这使他们远离了艺术家的诅咒。“我们被带有悲剧色彩的作品所吸引,但我不认为我们是悲剧的。我们都是非常积极的人,充满希望。”“死亡是终极之谜,”德尔菲娜说。江户补充说:“但我们不会避免它,也不会变老。”
然而,即使是在这种从沉闷的生活压力中流亡出来的过程中,阿根廷的政治现实以及备受争议的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也悄悄进入了对话。德尔菲纳认为他的价值观和政策可能是“危险的”。专注于纯艺术的江户补充道:“我们有很多朋友是电影制作人、作家、画家,这对整个艺术行业来说非常糟糕。但我们还是乐观地认为,一切都会恢复原状。这种情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微信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